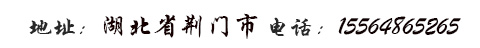拖刀面缸炉烧饼云头儿咱石家庄西部的
|
★拖刀面——大刀演绎痛快淋漓 面条本来寻常无奇,但井陉核桃园的拖刀面,因工具独特,技法独特,面好吃,现已列入市级非遗。我有幸吃到了这种面,在核桃园村吴福新家里。 核桃园离山西只有五里地。吴福新的小院收拾得一尘不染。70多岁的他在众人帮忙下,从二楼运下来长约一米五的大擀面杖,比擀面杖还宽的大案板,以及两条木凳。架好案板,老吴开始和面。他兑了一盆加了盐、碱的温水,徐徐倒入面粉中,和成颜色淡黄的一大块硬面团。老吴说,加盐碱是为了面条口感脆爽筋道,盐碱比例适当是和好面的基本条件。另外,手劲儿也很重要,和面要达到“三光”境界:盆光、手光、面光。 面团放置一会儿,饧好后,老吴操起擀面杖,将面团首先压成长方形,再卷起来徐徐擀开。恰逢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小组的4名志愿者也来拍照,大家兴趣颇浓,轮流上手试了一把,结果一致感慨:太费力气了!光靠往前推不行,还要用手按住面皮往下压、往两边压,怪不得过去这活儿专属于男性壮劳力。最后老吴将面擀成宽约八十厘米、长约一米五的一大片,在案板上铺厚厚一溜玉米面,将面皮垫在玉米面上层层叠好。之后拿出独门“武器”:特制大刀。只见这刀,长约60公分,由刀槽和刀片组成,刀槽的一头是刀把,另一头弯下来,在底端铸成一个圆形平托。因大刀太沉,拿不起来,切面时需握住刀把,来回拖动,故名拖刀面。拖动过程中,那圆形平托始终不离案板,自然而然起到平衡的作用。 说着容易做着难。切面时我们每人又轮流上手试了一把,发现切完总是把层层面皮压的快粘到一起了。最后悟出:要靠刀自身的重量往前滑动着来切,而不能刻意地往下压着切。老吴切面刷刷地,看似不慌不忙,其实速度很快,切出来的面条粗细均匀、不连不豁、四面有棱。整齐地码在盖帘上,看了让人馋虫大动。 那天八个人大概吃掉了四五斤面。在这里,我彻底了解了手擀面和机制面的区别。机器轧面,只刚刚把面和成团,即上机器压,可以说是硬挤压成的,所以难煮。手擀面的面团经过饧发,外筋内软,开水滚两三滚即熟。那天,吴福新的大女儿在家,做了西红柿北瓜卤,又另炒了两个菜。面条端上桌,大家经过一上午学习擀面的“体力劳动”,已经很饿,还好我没忘先拍照再吃。至于吃的感受嘛,我敢说,单就面条而论,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面。过了水的面条入口极其爽利,嚼起来微硬,但不是让人胃里难受那种硬,吃下去舒服、痛快,并且比较“坚饥”。像傅振华、吴福新这样的老人,对各种主食的耐饿程度了如指掌,耐饿即“坚饥”。拖刀面吃两碗,到下午六点刚好饿了,不积食,还坚饥。 “以前井陉农村,过事儿没有酒菜这一说,只有亲家席有酒菜一桌,其他多少人都是一碗面管饱。供应这么多人同时吃面,自然要‘大家伙’上阵。”傅振华说,拖刀面可以说是过事儿专用产品,要好几个壮男子配合,有人专事和面,有人主擀、有人配合擀。吴福新儿子结婚时,用了21袋面,七八个人分工,供大几百口人吃。现在人们图省事,都买机器面,吴福新虽然教了四个徒弟,其实这手艺在家乡已无用武之地。好在成为非遗之后,有饭店看上它。去年3月,吴福新第一次背着大刀离开家乡,到县城为一家饭店做切面。后来又到辛集一家饭店干了一个多月。因种种原因,以上两家饭店生意并不红火,老吴离开了。但今年,又有本地旅游区一家饭店有意请老吴过去。照目前这态势,拖刀面将不愁“面香巷子深”。 ★那关于缸炉烧饼的记忆 来井陉之前,我本以为平山的缸炉烧饼最正宗,但傅振华说,井陉的缸炉烧饼别具特色。那天我没吃早饭,到了县城先吃他买的炸油餜,又吃缸炉烧饼。油餜和油条做法一样,只是形状不同,井陉这里喜欢做成双股圆环状。缸炉烧饼和市区卖的外观上无差异,市区的缸炉烧饼有两种,一种是死面的,一层一层,能吃出面香。另一种是油酥的,吃起来酥,油香大于面香,但缺少嚼劲儿。那天,我竟没尝出来井陉的缸炉烧饼到底属于哪种,它既有死面烧饼的层叠,又不像死面烧饼那么硬,感觉更像是介于两者之间。 即使傅振华拣县城里做的最好的一家买来给我尝,它也仍然不是过去正宗的井陉缸炉烧饼。过去那种做法已经消失。城关河东村,曾有一户卖烧饼的,祖传技艺,打的烧饼放十天半月不返潮,不变硬,油不外浸,新鲜程度和刚出炉时略无二至,因此供不应求,逢城关集日还要多打一炉背到集上去卖。因城关是古驿道南北二支线汇合处,过往商贾众多,井陉缸炉烧饼的美名由此在山西、河北两地传播开来。人们知道好吃,但不知道秘笈所在。直到上世纪30年代,有一姓池的外地人迁居河东村,以杀驴为业,曾将驴油供给这户打烧饼的人,因同在一村,距离近,用驴油和面的秘密才渐渐被村民知晓,流传开来。 微水、罗庄等古驿道经过的村庄,过去有很多卖烧饼的。石太铁路修通后,两村商户把烧饼拿到火车站卖,借着东来西去的旅客,井陉缸炉烧饼的名声传播得更远。罗庄王三小做烧饼尤其好,火车一到站,乘客下车抢着要,有的提整包买。年6月,中共石家庄市委通知井陉派人到市里打烧饼,招待中央首长。县里推荐王三小去,打了七八天烧饼,回来以后才知道,是周总理来了。事后市委给王三小寄来立功喜报,还让地方政府安排好王三小,以发挥他的技艺专长。 “现在驴肉贵了,驴油供不应求,打烧饼的基本上都改用植物油了,酥脆劲儿和以前差不多,但是清香和回味感差了不少。”傅振华说完,讲了一个当地广为流传的吃烧饼的故事:相传清末民初,两位山西客商经过井陉,慕名到河东村饭店吃烧饼。几个烧饼风卷残云下了肚,还没吃够,见落了一桌烧饼渣,不由得馋涎顿生。可捡渣吃多不好看,一人急中生智,与同伴谈起自家房屋建设,一边说一边用手指蘸口水,在桌上画房屋结构图形,粘起的烧饼渣,再蘸口水时就顺便送入嘴里。其同伴心领神会,也在桌上所画图形之空旷处,添画门窗炕灶一类,直到把饼渣和芝麻沾完吃净为止。 这还不行。因为饭桌系阵年旧物,木头开裂,饼渣落到缝里够不着,咋办?一人突然惊呼:“哎呀!”用手猛拍桌边,说:“这里忘了留水道!”落在桌子缝里的饼渣硬是被震了出来,弹到桌面上,那人一边画水道一边沾入口中。另一人受启发,大呼:“这个房顶上还缺烟道哩!”也拍桌子。几番拾遗捡漏,二人终于志得意满,出门飘然而去。 ★云头儿——面做的艺术品 烧饼和面条用的白面,并非精粉。在白面紧缺的年代,仅有的一点白面也要分出等级:用细箩筛出的“头箩面”,相当于现在的富强粉,用于炸油条、包饺子、拉面、蒸“递期馍馍”、祭祀蒸“供享”。递期馍馍是娶亲前男方给女方家首次馈赠的礼物(递期,商定娶亲日期之意),特别讲究排场,用专用模子脱制,顶上印红双喜,四周花纹沟棱相间,一个馍馍大到用八两至一斤白面。祭祀蒸的“供享”做成各种人物、动物造型,染上颜色,和山西的面塑艺术是一样的,秀林镇南张村曾办过面塑展。 或许因为网上山西面塑照片很多,面塑没让我有啥触动。让我惊讶的是“云头儿”这种面食,傅振华怎么跟我说,也不明白,回头他专门找人做了拍照片传过来,一看照片立即明白。这绝对是细粮精做的代表了:和两块面,一块普通白面,一块加红糖或甜面酱和成红色,两块分别擀成薄饼,叠在一起卷起来,再切片,断面红白相间。这样如层层花纹一样的食物够好看的了吧,还不行,还要用两手各拿一双筷子,在入锅炸之前,逐个将椭圆形面片夹出几个凹来,夹完之后,变得和画上的云朵一样一样的。 这样的艺术品不像面塑只在极特殊场合专门做,这是南陉、孙庄一带过事儿时广泛食用、批量制作的艺术品。类似的还有面筋、假肉。面筋不像别的地方把淀粉洗出去,这里直接加入绿豆芽、葱花、盐等,和面上笼蒸熟。熟后豆芽收缩,面体暄软,切大块油炸,过事儿时当主食,咸香诱人。假肉只加调味品不加菜,面质紧实,能切得更小,炸出来更像肉片。它和云头儿同为大锅菜里肉的替代品。 井陉是一个民俗文化异常丰富的地方,物质的匮乏并不妨碍精神的丰厚。就像云头儿这样的食物,不光是味觉的享受、视觉的盛宴,更是智慧的闪现,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稿件转自微微第一庄) 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ijiazhuangzx.com/sjzfa/7769.html
- 上一篇文章: 一条微信吃遍石家庄的特色经典美食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