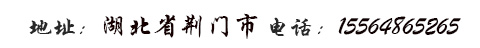韩信井陉背水之战,战场寻踪刘育书
|
韩信井陉背水之战,战场寻踪 刘育书 公元前年,韩信和张耳率领三万汉军在井陉绵蔓河畔背水设阵,击败赵王歇和陈余统率的二十万赵军,赵王歇被擒,陈余被斩,赵国灭亡。那么,当年背水之战的古战场在哪儿?现见诸文字的说法有四处;微水、威州、天长镇(原井陉城)、鹿泉(获鹿)土门。对此,笔者谈谈个人的看法。 土门之说这是不久前有人在网上撰文上提出的。此说是无稽之谈。鹿泉土门,历史上被视作井陉关、井陉关的东口,此距井陉微水约30华里,距井陉威州(走西北向的白鹿泉、胡申、段庄、平望一线)还不足30华里,直线距绵蔓河(若不计中间的山岭、沟壑)大约25华里。土门一无河二无水,如何背水列阵?若说在此屯军,安营扎寨,把守井陉口是有可能的;或说韩信背水布阵前,赵军的大本营已扎在土门-胡申-平望一线还沾点边;而背水布阵,其地理环境是不匹配的。 天长镇之说此说可能与两块石碑有关。一是明万历廿九年(公元年)由霍鹏为井陉城西关新建淮阴侯祠所撰文的石碑。但碑文中只是对韩信作了极简的评述,未提及背水列阵一事。再一是旧城外河东坡村曾立有“淮阴侯谈兵处”石碑,碑石的文字为“明崇祯戊寅(公元年)中州范志完题”。河东坡村位于山西到井陉境内的古道上,从这里开始又分为南、北两条路。有可能汉军行至这里,韩信曾给部下讲说兵法,或是在此将部队分为两路,主力走北线(主道),二千轻骑走南线。韩信是否在此讲过兵法,没有确凿的文字记载,只是传说;公元前年至公元后年已隔年,后人有好事者在此立碑不过是为弘扬这一“美丽的传说”罢了。这两块碑石只能表明韩信曾率军路过此地或在此屯过军,若说在此背水列阵是不可能的。此处绵蔓河床狭窄,难以布阵、摆战场。 威州之说著名历史学家李开元教授持此说,为之撰写了《背水之战》和《井陉访古寻战场》(载《楚亡》第三章)。作者年6月曾赴井陉实地采访,寻找当年的古战场。客人来后,井陉县委史志办和县文管所都给予热情地协助,得到“教示引导”(李原话)。经李先生实地走访,他感到井陉县内,战国秦汉的古代遗址,都集中在北路上。说“这一条道路,才是战国秦汉以来的井陉古道。威州镇北岸村北,有威州古城遗址,筑成于战国时代,是中山王国南部镇守井陉道的要塞,古称蔓萌城,在赵国与中山国的多次战争中,这里都是战场。”认为“威州古城遗址在绵蔓河东岸,不但控制着出井陉道北上通往中山国(今平山县)的要道,也是扼守出井陉道东去通往赵国(今鹿泉)的要塞。可谓是古井陉道东边最重要的关口,陈余军的驻地,应当就在这一带。威州古城与绵蔓河之间不过两公里,地势开阔平坦,正是一处可以摆弄阵势决战的古战场。于是遥想当年,站在威州城头的赵军将领,望见背水列阵的韩信军,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本人完全赞同李教授此说。 微水之说文字资料主要见吴文楠撰写的《确考汉淮阴侯韩信背水阵故里碑记》。该文先后转载在雍正八年修《井陉县志》“艺文志篇”和民国廿年修《井陉县志料》“金石篇”中)。吴文楠浙江海宁人,康熙廿一年至廿八任井陉知县,碑刻于康熙廿七年。其“确考”的主要依据是《史记·淮阴侯列传》中,“侯欲下井陉,赵王、成安君陈余聚兵二十万于井陉口。侯未至井陉口三十里,止舍”等语。吴知县便以“微水离土门恰好三十里”加以论证,断言得出“今证诸史,而以舆地细按之,阵在微水村之地确然无疑。”个别文史爱好者也持微水说,证据是白石岭上建有陈余祠、墓和立有相关的碑刻,在微水一带出土了汉代兵器等等。 一位历史学家曾说:“历史不可以回转,历史却可以体验,现场考察的实感,可以超越时空,再现历史的形象,诚然信矣!”又说,“历史不仅是往事的记录,也是对往事的解读。”对上述四说,古战场不在获鹿土门村和井陉天长镇没有什么可争议的。这里本人仅以亲临、所见,对“微水说”和“威州说”谈谈个人的看法—— 从实地所看到的吴《碑记》文中说,“由白石岭望微水则见,白石岭望威州镇则不见。”“背水布阵断然不在威州。”吴知县在井陉任职8年,不知撰写此碑文前是否登临过白石岭,是否脚踏过青石岭,是否涉足过威州至平望的路?还有,吴知县很可能没去过或根本不知道井陉界外紧连获鹿县境内另有一条通往井陉的道路,即由土门经白鹿泉、平望直达威州的路;而青石岭下这条北路经威州、过平望到土门,大约也“恰好三十里”。年至年,本人在威州工作和生活,多次穿行在威州至南、北平望间。这段路,视野开阔、相对平坦,远比由微水去白王庄翻越白石岭轻松得多;而出平望村不远即是获鹿县境,若右行走段庄、胡申、白鹿泉等村,大约10华里便到土门村。我平望的学生说,他们村的人经常直接从村东下(去)获鹿赶集,若去石家庄就走段庄、白鹿泉、土门这条路,很少绕威州、经岩峰、过上安走国道。再则,你登上威州南沟、寨湾村后的土垴(俗称猴山),不但对宽阔的绵蔓河一览无余尽,还可直接观测到河对岸的固底等村和青石岭一线。常听当地人说“城里地”是块“风水宝地”,是指北岸村后红旗厂所占据的地方。此处地势不但平坦,相邻的簸箕掌(山)还将它紧紧揽在“怀里”。这块“宝地”,战国时属中山国,建有蔓萌城;有专家考证,以此为中心还建立过绵蔓国,辖今天部分井陉、平山、获鹿地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红旗厂建厂打地基时挖到不少古墓和出土不少文物。我经常进入厂区,面积约2平方公里,还不计其围墙外的训练区。 年本人由威州调县城工作,之后连续两年在白王庄(时称向阳)学校蹲点,微水距白王庄最短的线路就是翻越白石岭,已记不清走过多少次。那时白石岭上的东开门、戏台、茶棚及其陈余祠、陈余墓、碑石等等都已变成废墟。记得荒草丛中的陈余墓,石碑后不是坟丘而是一个大坑,很可能“文革”中破“四旧”时被挖掘过。站在山岭顶上,是望不到绵蔓河的,更甭说能观看到调兵遣将“背水布阵”了。山岭上那些已变为“废墟”的古建筑大都是明、清时期的,还有民国年间的。至于说此地发现过汉代的兵器不足为据,绵蔓河沿岸多处都挖出过,下游的段庄、东元村等地发现的文物更多,而年代更早。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ijiazhuangzx.com/sjzfa/13534.html
- 上一篇文章: 带你行万里路之萌妈版山西亲子游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